冒失的童年散文
我们火烧泡子屯是1970年底才开始通电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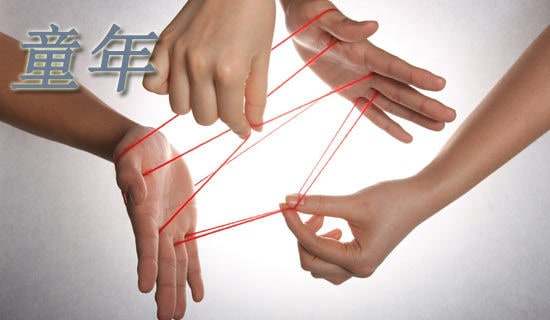
第一印象就是电灯,与过去的电灯比,真是亮啊!生产队也有了磨米机和粉碎机,省工省力。从此,我们告别了“油灯照明,毛驴拉磨”的时代。那时候我七八岁,对电的知识并不懂。通了电之后,电工对社员,家长对孩子,便进行了最基本的用电常识的普及。而我还是懵懵懂懂的,只是觉得电的力量很大,无所不能。
年底的一天,父亲扛着半面袋子苞米去生产队的磨米房,我也跟着去玩儿。磨米房里机器噪音很大,说话得大声喊。我看见有人正在用磨米机给谷子去皮,小米从机器下边的漏斗里流出来。等磨完了,电工就拉下闸把机器关了,但磨米机与电机之间那宽宽的传输带不是立马停下来,又笨重地“啪嚓、啪嚓”转了好些圈。
接着,磨苞米面的粉碎机也磨完了排在父亲前边那一家的苞米面。当电工拉下闸时我发现那三条并排的三角带仍然飞速运转,大约30秒后才停下来。电工抖动着磨面机下边的大布口袋,把苞米面导入那家的面袋子里,然后又将我家的苞米倒进机器上面带有漏斗的大槽子里。接着他过去推上电闸,机器又嗡嗡嗡地工作了。
我走进电工喊着说:“重开机器多麻烦啊!关上漏斗就行了呗。”电工挠挠头,看着我父亲,然后笑着向我伸出大拇指。
我很得意,其实我并不希望有再来磨苞米面的,因为我心里正在盘算着一个新的设想。
终于等到我家的磨完了,电工拉下闸后抖出袋子里的面,父亲用我家的面袋子接着。三角带还在借组惯性抖动地运转,速度在缓缓地减慢。我估计它应该就要停下了,便上前一步,伸出右手,用足力气,一把抓住那三根三角带……
机器停下了,但我的手指已经夹在三角带下的轮槽里,同时我“哎呀”一声。父亲和电工跑过来,他们往回倒三角带,把我手弄了出来。父亲活动一下我的每一个手指,看没有什么事,便打了一巴掌。
回家后,父亲带我到赤脚医生周大舅那里看看。周大舅看了看,说没什么事,只是大拇指被咯得有些肿了,便给我抹了些有怪味的黄药水。他开玩笑地夸我敢于冒险,为此奖励我一付劳保用的大手套。
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,一个周末的早上,父亲让我把院子彻底清扫一下,然后他把两麻袋苞米粒子倒在院子里,又摊开了。
“苞米有些潮湿,天暖了如果不及时晾晒就容易发霉。”父亲说完就去队里上工了,临走时又嘱咐我,“一定要照看好苞米,别让猪鸡什么的给祸害了。”
那时候乡下条件很差,家家户户的篱笆都是秫秸墙,不结实,到秋天就拆掉做烧柴了。因此整个冬季到第二年春天种菜前,院子都没有什么遮挡,常有禽畜出没。
我找来个长木杆子,在一头儿又拴了段绳子,就做成个简陋的大鞭子,搬个小凳子坐在那里。来到这里的禽畜见到苞米起初跃跃欲试,我摇一下大鞭子,它们就不敢靠前了。有那么一会儿,我去房山头撤泡尿,回来就见一只胆大的公鸡带头吃起苞米。我来不及甩鞭子,直接把鞭子扔过去,吓得它们一蹦老高地跑远了。
在那坐了一阵子,觉得没什么意思,我就回屋对母亲说:“外边冷,屋来暖和暖和。”
我坐在地桌前,看到父亲用布条子缠的台灯电线接头儿,就打算把昨天从电工那里要来的黑胶布换上。这盏台灯是父亲为了方便我们写作业,自己制作的,缠在接头儿的布条子外边又绑着一圈圈的棉线,我捅咕了半天也没拆开。此时我一直担心院子里会不会来猪或鸡什么的',情急之下我决定把它剪断重接,再用黑胶布包好。我找来剪子,对那个接头正要用力时,母亲在厨房突然喊:“快!快!猪吃苞米了!”
我把剪子一扔撞门而出,把那头猪撵出去很远很远,我想累累它。不是说猪跑累了就掉膘吗,我不能让它白白地偷吃几口我家的苞米。
撵猪回来,我累得一身热汗,筋疲力尽,估计我自己也减肥了。我趴在地桌那喘了好一会儿,闲不住的手,就拧了一下灯头上的开关玩儿。灯突然亮了,把我吓得一哆嗦,坐在那里,接着又出了一身冷汗。
原来灯线上是有电的啊!这时我才发现,刚才竟然忘了把那头的插头拔下来。
不敢想象,如果不是母亲喊我快去撵猪,我一剪子下去,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我蔫蔫儿地收起剪子和黑胶布,老老实实地到院子里照看苞米去了。
由于那时候常常停电,因此煤油灯并没有立即扔掉,不过供销社已经不再卖煤油和制式煤油灯了。
制式的煤油灯,是玻璃的灯罩,金属的灯头,还有控制灯捻子上下的小齿轮。棉捻伸到下方的煤油里,可以把煤油吸上来,只要用火柴点着灯捻子上边的头儿,灯就亮起来了。
没有电的年代,多数人家买不起制式煤油灯,一般都是自制的。有时候在煤油灯下贪黑写作业,家里一盏灯不够用,我便用墨水瓶自己做了个小煤油灯。找个不怕热的汽水瓶盖,换掉墨水瓶的塑料盖,用粗钉子在汽水瓶盖上打个孔,用钢笔囊的铁外罩做灯芯模,插到汽水瓶盖的圆孔里,再用旧鞋带或捻个棉花捻子穿进灯芯模,墨水瓶子里倒上煤油,一盏简易的煤油灯便做成了。
一个雨后的傍晚,有个城里开来办事的大汽车陷进屯东头的坑洼处,那司机多次加大油门,但就是出不来,还越陷越深……
我跑回家,把家里的一把铁锹拿来,借给司机师傅。他挖了一阵子,终于把车开车去了。他说着感谢的话还我铁锹时,我笑着递给他一个空汽水瓶。他立马就明白了,把我的汽水瓶伸进油箱,给我灌了一瓶汽油。
有一天晚上停电,我便点上了汽油灯。那天作业多,写到很晚时,画图用的三角尺不小心掉到地下,我端着灯找的时候,胳膊不慎磕碰在地桌腿上,结果手中灯里的汽油喷溅出来落到手上,可能是与灯火太近,手上的汽油就着了。我急忙放下灯,用另一只手去胡噜,没想到那火就换到另一只手上。等我终于把手上的火弄灭,发现地桌的一条腿起火了,火在往上窜,眼看着就要超过桌面。
当时家人都已经休息,我急得不行,记忆里好像听说过扑灭油火的办法,但没有实践过,我便到炕边一把拽过盖在弟弟身上的棉被扑到火上。
火,终于被我扑灭了。
惊醒的母亲问:“屋子里怎么这么大的汽油味?”
我说:“刚才把油灯碰洒了。”
父亲说:“半夜三更的你瞎折腾啥呀?想把房子给我点着啊?”
我赶紧上炕睡觉了。心想:刚才的一幕你们没看见,还真是差一点没把房子给你点着,吓死人了。
童年时的我,即淘气又充满了好奇心,见到什么东西都想去捅咕捅咕,总觉得自己什么都行,常常不去想会有什么后果,所以也惹了不少的祸。如果当时剪了电线,如果扑不灭那汽油火……太多太多的如果,现在想起来还觉后怕。难怪当年母亲感慨:“这死小子,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!”